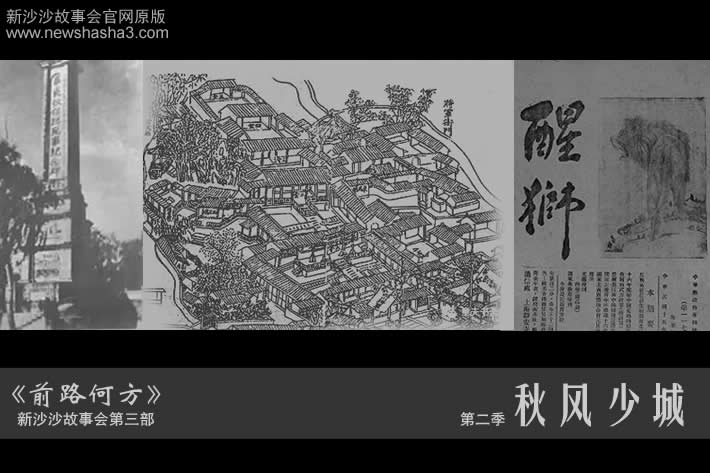
第1部分
=================================
从K行出来后,我边往地铁站走边给鸡屁电话,约好中午一起吃饭。这娃现在是上海朝春小学的数学老师,你妈简直要把老子腰杆闪断。神仙都想不到这个带黑框眼镜,一副文质彬彬样子的小学老师十来岁时竟然是成都的少城街娃,满满还以手黑心狠出名。鸡屁现在说四川话已经不咋个流利,但听还是没问题。在饭桌上我说四川话,他答普通话,喜剧的很。喝了点儿小酒,他下午还要上课,不敢整凶了。到后来我们说起张坷,都很遗憾在成年前就失去了联系,不知道他现在好不好。
我对张珂和鸡屁的感情,跟江海瓜皮唐益不一样。我们三人都是炮党后裔家庭出身,在少城那个环境里,更有一种感同身受的相惜感。
聊到后来,鸡屁突然一拍脑袋,猛然想起去年在浦东机场川航的柜台见过一个女孩子,摆出来竟然是二毛的侄女,让我晚上去机场时顺便找找,说不定能打听出张坷消息。二毛是女生,我们当年西马棚小学同学,唐益的小学闺蜜,但初中上的体育场那边的24中,而且慢慢成绩变好了,后来就很少ka过东城根街到少城这边来耍。她和张坷是一个民航院坝的,中学时代盛传两人好过。
下午鸡屁回去上课了,我回酒店前台拿了行李,上地铁,倒出租,倒黑车,折腾到傍晚,回到那家破败的度假村,把那叠资料交回给了对方。那娃面无表情,也没清点,不过却很意外的伸手出来。我一怔,犹豫了下,也伸手同他握了握,然后转身走人。
晚上在机场,鸡屁说的那个女孩子不在。我让柜台里的同事给她打个电话,没想到这女孩竟然死活不愿老子在电话里和她说,只让同事一句一句的转述。我说了二毛的名字,说了是小学同学,想找人,甚至还准确说出了以前张坷和二毛住的羊市街民航宿舍。女孩子过了会儿才在电话里把二毛的号码告诉了同事,转述给我,至始至终都没和我通过话。我记下号码后,问柜台内的川航同事,这女娃儿是不是长的很乖?同事一怔,你咋个晓得?老子答,日妈美女硬是要欧上天!同事笑笑,没说什么。
在登机口我还给鸡屁打电话“你妈那个二毛的侄女咋个那么欧?我面都没见到竟然还给老子端了一哈。你娃咋个和别个摆的到那么久,还摆出了是二毛的亲戚?”
鸡屁哈哈笑“所以你从小就不招女生喜欢呢,现在这些年轻女孩儿,都喜欢和嘴巴甜的撩,像你那种几句话就骂娘的还撩个P啊!”
回来后通过二毛,在07年最后一天终于联系上了张坷。那天傍晚收到个陌生号码电话“背娃儿!”
我愣了下“哪个?”
“坷娃儿的嘛,听不出来了啊”
“日你娃咋个口音都有点变了”
“在重庆十多年了”
“安,在重庆啊?”
“是嘛,我93年参加工作就在重庆,这好多年了嘛”
张坷从广汉空乘班毕业后参加工作就分到西南航的重庆公司,几年后出来了,跟到亲戚做酒水生意,西南几个大城市,重庆成都昆明贵阳到处跑,99年抓住五十年大庆的机会整了几个海单子,小发了哈。后来亲戚要回贵阳,他就买了亲戚在重庆的几个房产中介铺子,长期专做二手房了。酒水也在做,只在南岸留了个精品铺子,秧起,主要是他贵阳的亲戚在猫台有关系,他这边留个铺子就是偶尔弄到欺头用来散货的。
我这次回成都其实只能呆两三天,但西环线那边一直没给我把手续办好(后面会讲),打电话来要求我随时准备去澳门,说是联系了个法语老师给简单培训下,结果也是一拖再拖,有一出没一处。和小欧Q了半天,他娃也说不出个所以然,都他妈懵逼状态。我想想,国企风,和北角两回事,习惯就好……后来老子脑袋一转,给西环线说,我自己找个法语培训,半个月,行不行?那边nod。于是老子就跑去川外(在重庆)报了两周的成教速成班。嘿嘿,正好去会张坷。
十四年了,两个朋友重逢后不甚唏嘘,晚上就在北滨路冷淡杯整了好几件啤酒,一直聊到天发白。
摆到海娃儿枪毙,感概万端。张珂说,他后来听二毛讲起过,橙瓦街派出所的人说“那伙街娃儿只枪毙了一个,算运气好,全部弄切塔子山就对了,这条街要清净的多”
老子骂“日他妈,我们又没害过人!”
张坷接上“是啊,你妈那年代有几个没在街上操过嘛,说得好像出了少城就没得街娃儿一样”
张坷因为早早去民航上班,鸡屁更早就回上海读歪师范,我考上了大学,所以和江海瓜皮走的路不一样。在这里重复青春第一季初恋故事完整版中的一句话,少年到青年时代的分野,可以决定今后一辈子的人生。
不过有件意外的事,张珂说他2001年在成都红牌楼修车时碰到过诚娃。这娃当时穷困潦倒,帮生产队开车行的亲戚洗车(他们是红牌楼农转非)。张坷初二的时候因为长的帅,惹些花案,江海出头带人去和玉带桥的整,诚娃来帮过忙的。张坷看诚娃现在如此潦倒,就抽了他一把。当时张坷要转型在重庆做二手房,手上在成都还有批酒,就报了个友情价,让诚娃帮到销货,安心让他挣个跑腿费。
张珂把前前后后一讲,我才知道原来当年出事,诚娃根本没被抓,当天嗅觉灵敏跑的快,江海枪毙后他才敢回成都。在外躲了一年多,把身上钱也全部用完了。当时唐益已经被姐姐带去马来西亚做生意,诚娃当年混社团完全是江海带着他操的,现在海娃儿死了,唐益走了,他没其他社会资源,红牌楼普通农转非家庭,只好回红牌楼帮亲戚打工混日子,穷困潦倒,幸亏碰到张珂。诚娃还在一次酒后告诉张珂,我们十来岁那次百花潭后门群架被抓后,他自己在少管所只有一年,比江海先出来,海娃儿让他回成都后帮到照顾下唐益。结果他妈就和很多电影中的桥段一样,诚娃回来按江海说的去找当时成都很火的盐市口那个夜场的一个看场的江海的熟人,跟到看场打杂,挣点生活费。唐益当时没读书了,但又还没等到他们铁路局内招,就在屋头耍,时间多。诚娃经常把她带去上班的夜场免费玩,结果一来二去,就喜欢上了唐益。人家唐益是铁路局大单位的,以后有工作,当然看不起诚娃这种农转非,但又没明确拒绝,反正就那样一直腻起。
我听张珂讲到这,楞了好久,然后说“锤子,老子不信!”
张坷说“你娃晓得个球,你上初中后只有假期才回成都来,其实对长大后的唐益根本就不了解。女娃儿的心思嘛,我清楚的很…..”
我想了想,问“那海娃儿从简阳(少管所)回来后晓得不?”
“这个就不晓得了嘛,估计看出来了有点暧昧,也不好说啥子。唐益当时已经上班了,进京车,一枝花。海娃儿当时还没混出来,本来就有点怕自己拖累了唐益。其实唐益看诚娃连备胎都算不上,按现在说法只能算舔狗,免费劳子。江海更不好说啥子,还对诚娃有点内疚,一直带到诚娃操……海娃儿心好,外狠内善,是老子早就给唐益撕破脸了!”
我灿灿的对张珂说“你从小就不咋个喜欢她,成见嘛”
张坷说“成见个毛!小学西体打架的时候就给你讲过,你一直对唐益好,但唐益可没你以为的那么对你好。只不过你娃见不得女的欧起,随便哪个女娃儿对你软点,硬是就当成个宝……你妈哪个女娃儿不欧嘛,稍微漂亮点的都喜欢端一哈,好正常嘛!”
我说“塞,老子又不像你是上过天的帅哥,身边随时都有妹妹围到转,妇女之友唆…..唐益对我至少还是算够朋友三”
张珂撇嘴“够朋友?你不晓得唐益对你当年连累海娃儿少管一直有怨气?你想嘛,从小就喜欢江海,十来岁的女娃儿,最相思的时候,结果男朋友被弄你妈到简阳切关三年,里头至少有两年是帮你娃关的嘛……我们原来西马棚的班主任在香港回归那年得癌症死了呢,他们在成都的都去过,唐益也切了的,给二毛说你高中躲到郊县连信都不敢回…..不然你想哈为啥子后来你们帮江海跑路出事,她要喊诚娃给你安桶儿嘛,也是做的出来哦真的是……”
我一愣“啥子桶儿?”
张坷很惊讶“我日你不晓得啊?”
我更奇怪“晓得啥子?”
张珂想了想,犹豫了一下,还是慢慢说了出来。
原来我们那盘出事,我从苏坡桥回城找人拿到药后,给江海电话问下一步咋办,唐益偷偷在旁边给诚娃打了电话的,让他接到我后小心点,怕我生变数,最好给老子安个桶儿。诚娃后来酒后给张珂说的唐益的原话“不然他可能又会跑,人家是大学生,万一有其他想法,一哈刚不起,整砸了,这次难道又让海娃儿给他背!?”
我看着张珂楞了半天,猛然一下想起当时在宿舍里那个留给同事的纸条。景查说没查到啥子纸条,还一直问我根本就没见过的几千块钱,当时我感觉好奇怪……怪不得我和诚娃急慌慌的抱起东西跑下两层楼后,他娃突然又说要回去上哈厕所,然后等了你妈半天才下来……老子一个人在院坝头车上守着药水瓶子紧张的发抖,手揣在包里攥着七七,枪把上全是汗,握都握不住…..我不敢相信,或者说,是不愿相信当年隐隐约约就怀疑过的事(当时在宁夏街看守所,死皮哥听我摆龙门阵说完经过,就提醒过我景察不会无缘无故问些你不知道的事情,你娃多半被人安了桶儿,外地朋友不懂这话的意思也不要再问了,我实在是不愿意再回忆再解释意思)。人生三十多年,完全没想到从小就当异性兄弟的人竟然会如此提防自己,甚至根本就没有真心把我当兄弟……用现在小孩的话说,一万点暴击!
诚娃没那么多脑花,很难自己想得出来这种做法,再说老子和他无冤无仇,他也犯不着主动这样做;江海更不可能,真这么阴会十来岁就帮朋友顶罪?这种阴人的玩法在二十多的年轻人中玩出来,只可能是女人的主意,内心长期积怨得不到释放的后果。张坷说的对“你不要以为唐益这样做有啥子内疚,一点也没得!她反而可能还会觉得心安理得,认为你欠了她的,你付点代价公平合理,天经地义!”
我确实没法说什么。只能把这一万点暴击默默吞了,今后余生当没有过这回事。
青春,别再见。
在重庆游神一样晃荡了半个月,法语课根本就没听进去(半个月本身也学不到啥)。内心矛盾痛苦不堪,青春年少的很多坚持变得……也不能说没意义,只是太让人不舒服。社会就是这么现实,人心就是这么不可知。31岁的我已经年过而立,照理应该对很多东西有心理准备,但真当自己猛然面对时,还是难于接受,只能强迫自己接受吧。又能如何呢?
走的前几天,还用当时全部的家当托张坷买了个八十多平的二手房,完了身上甚至只有不到一万块。那几年国内房地产早已开始起飞,我却一直没自己的房子。几年前在成都和周越按揭买的那个新房在分手后就立即卖掉了。当时不规范,还可以转按揭,我为了尽快解决掉成都的尾巴好动身去香港,只能让售楼MM帮忙原价转让出去,还自己给了几千块的手续费,只收回来了一点点钱(买的时候成都房价很低,又只有20%首期,所以钱很少)。现在想着以后如果能全身而退,就回四川退休;另外心里还对方雅抱有幻想“如果真有那一天,至少得有个房子,不然难道回成都和家里挤?”重庆的房子比成都便宜,只买的起这个。重庆就是四川,除了比成都热点其他没啥大差别。而且我此时的身份有很多身不由己,所以就算以后能全身而退了,也不太愿回成都,想换个环境生活。
动身去香港前一晚,和方雅电话聊了半宿。告诉她在重庆买了个小房子,以后要是混不下去了就退休。方雅问,去重庆生活啊?我赶忙改口,你要是没嫁人的话我就把房子卖了来上海找你。方雅回你得了吧,说不定哪天又联系不上了。我内心一下变沉重,除了玩笑话,也感觉真有可能,毕竟前路未卜。犹豫了半天后,我决定把在北角的事告诉方雅,让她心安。毕竟现在已经反正,说出北角的事已经没有什么风险,至少对方雅说不会有太大问题(当然只是简单提了提,关键东西不可能说太透)。
我在电话里沉默了一下,然后开口“我,我想……想给你讲件事”
她嘻嘻笑“怎么吞吞吐吐的……这么快就有女人啦?”
“别乱扯行不行,给你说正事”
方雅听完后倒是没怎么惊讶,还开了句玩笑“原来不是去西天取经啊,还以为你真当和尚去了呢”
我叹口气,没说话。
她好像在吃东西,吧唧吧唧的“骗我说什么鸡……很大很大的电脑……哦,主机公司,还副总经理,你靠这个蒙了不少女孩子吧?”
老子没好气“我这么笨的嘴巴,蒙个屁!”
“香港电脑公司老板,这名片一亮,深圳东莞不知道多少厂妹上着赶子往上扑,你当我白痴啊还信你没乱来过。肯定两周换一个,眼都挑花了。正好选一堆大胸大屁股的肥婆,满足你自打业余体校开始就对丰满女人的幻想。看一堆篮球肉弹大胸不把你闷死!”
我目瞪口呆,顿了半分钟不知道该说什么,最后只好冒一句“我说东,你给老子扯西……我讲的到底听明白没有?”
“有什么不明白的,不就是干些擦边球的破事吗,你们四大干这些玩儿还少了?”
这下我真没语言了,只好点头“行行行,你只要知道就好……还有,我没在广东乱搞,别他妈胡说八道!”
她一下嘻嘻笑“生气啦…..那我就信你”
又乱吹了会儿,她突然问“那你以后的工作是不是跟以前差不多?”
我没正面回答,沉默了半天轻轻说“最好还是……不要问这个”
“我才没兴趣知道呢,我是想说…..”
“什么?”
她噗呲一声“篮球大胸多不多?”
老子鬼冒火,没好气的说“有啊,多得很!你那小馒头还没别人乳晕大!”
她立即给老子挂了,我日。
没两分钟笔记本上QQ就叫,我点开一看,马上被锤子敲头表情刷屏,还刷了他妈整整三屏,日本人!
大学最后那年两人一起玩,一开始互相就感觉很谈得来,比跟程璐呆一起要随性得多。方雅放得开,荤的素的什么都能聊。有次晚上我送她回西外,走在长安南路上一时兴起,想起她当时还是处女,就滔滔不绝给她科普“运动常识”,一副见过大世面的样子,口若悬河狂吹牛逼。后来还互相说起自己的性幻想对象(记不清是谁开的头,很可能是她,当时她喜欢席慕容三毛汪国真这些人的东西,虽然自己从未经历过男人,但却表现得像个成熟御姐,属于大学女生里那种自认为肚里很有货的典型假老练)。我说我从小混业余体校,看女生肉最多的时候都是在夏天的运动场,所以对丰满健康有胸有屁股的女人一直有幻想。她说她从小就喜欢表哥,高大帅气霸道又呵护她还很洋气,以后一定要找个同款。然后两人就开始互相洗涮,她说老子是粗鄙土人,最好找个大胸大屁股的文盲村妇,白天下田,晚上上炕“既能生养又能把你锻炼舒服,一屁股坐不死你,多好啊”;我说她人瘦个子高,又没胸,本来就“平得很”,还是专业练舞的脱了衣服全是肌肉,这怎么让人硬得起来,你看我现在就没硬,连我都吸引不了还找什么帅哥。
方雅转头说老子XX(是个东北话词语,类似于现在的口嗨)“土人懂什么叫身材,懂什么叫韵味”来个骄傲小白眼“还别说我脸可能看,就算不看脸,光靠这身材就迷倒一堆人!”
我笑“得啦女神,这么牛逼怎么没见哪个帅哥追你”
她一脸不屑“外院成天腆着脸跟我屁股后面的男生至少一个排!待会儿送到校门就行了,要在学校里跟你走一块儿明天就是大新闻,我四年形象全毁了”
“一个排男生你都没瞧上?继续牛逼下去吧,老子看你多半要当尼姑……会跳舞的尼姑”
她继续白眼“尼姑又怎么了?就算当尼姑也不会跟看不上眼的男人说话!我就这样,打小就这德性”
老子怔了好一下,只能苦笑“行行,你高兴就好”
不过这里插一句,方雅在西安的时候真的非常瘦。我们那时候的大学你懂,食堂卖的比猪草好不了多少,年轻女孩子没父母看着,放飞自我,零食当饭吃,人瘦得来跟竹杆差不多。那时候她在演出队又坚持每天练功,像初中在黑龙江省歌一样,风雨无阻,运动量一直保持着。然后夏天时衣服一少,露出来的就全是精瘦肌肉……后来毕业在北京入社会工作后,那根弦才终于松了,功也没怎么练了,经常跟着公司同事一起吃饭油水也大,三年长了二十斤。虽然仍然非常瘦,但看起来勉强算是正常人体型了。我们2001年在国贸地铁站重逢时,开头那几秒钟我愣是一下没认出来,长发披肩(大学时都是盘着的),脸也圆了一圈,三年不见像是变大了一号……
过了十分钟,我在QQ给她留言“记住我在上海交代过的那些话,刚给你说的也不能告诉任何人,照顾好自己,有事电我”她没回,老子也懒得理,洗澡睡觉。
不知道过了多久,我都睡着了,手机响,方雅的。我迷迷糊糊问“又怎么了?”
“你不是说了有事电你吗,现在我就有事”
“到底怎么了?”
“我生气,睡不着!”
我叹口气,苦笑“行了行了,我最喜欢平胸,满意了吧?”
“不满意,我又不是平胸”
老子……我想了半天,只好说“大胸会下垂,哪能跟小馒头比,小馒头有气质啊”
玩舞蹈的最喜欢听别人说气质。这下才算勉强安慰住,好说歹说没事了。你妈的,一不小心就踩雷,桑爱女宁毛病多得很!
在重庆这半个月,我和张珂喝酒时还摆到近况。只给他说了在深圳广州混,做电脑生意的,偶尔去香港。我不会给四川的任何朋友说自己长期在香港,具体工作更不可能说了,甚至故意掩饰自己对金融产投方面的了解。张珂说他又离了,三盘。老子只能服气“硬是帅哥要杀杠点,你娃是不是走到哪都有女人给你捧起?”
张坷笑“老了,年轻的时候差不多”
“等于是在西南航的时候有富婆包?”
“包毛线,老子还想包美女呢,不当空哥了就是嫌钱少,想多整点钱才网得到妹儿”
我突然想起“对了,二毛是不是后来和你耍过?”
张坷扁扁嘴“哪有哦,就是从小关系好,走得近点而已……她老汉儿当过局办主任的嘛,把她弄到天津去上了大专班,回来安在油料(现在的航油),吃安胎钱,安逸的很,我高攀不起三”
我叹口气“记得你姑爹最早还是在民航当过官的嘛,没抽你一哈?”
“早死了,我刚去广汉上学就死了。老头儿还是造孽,抗美援朝的时候受过伤,身上有弹片,每年都要住院,纯粹拖死了的……”
张坷的爷爷叫张呈华(真名),彭县磁峰人,是一个地主家伙夫的儿子。老家地界是盆地和藏区交界的山区,所以汉藏通婚不稀奇。呈华的妈就是个藏女,是他老汉儿年轻时去松潘找钱时,从一个藏族老大手里买的。这藏女长的牛高马大,面目黝黑,干活是一把好手,呈华的爹老张认为这生意做得,毕竟当时农村,人力就是最大的资本。呈华生下来又黑又蛮,得一外号,张炭娃儿。老张是伙夫,揩点油正常的很,把娃喂得好。到炭娃十五岁时,已经和成年人一样高,甚至比成年人还重,五大三粗的一堆。
老张的东家也姓张,和他有点亲戚关系。这位哥是嗨过的,但基本不参与堂口的事,只是因为有点家业的地主,挂个名,保平安而已。东家偶尔会到通济场本堂堂口的茶铺上去吃两杯茶,和十乡八里的“头面人物”联络哈感情。结果有次去吃了茶回来,当天晚上就在床上吐血死了。然后报官,整了半天,查出来是被毒死的。堂口上的人其实很多知道内情,是东家和人结了仇,被人买通茶铺伙计在杯子里下了药。茶铺是袍哥堂口,显然是不可能承认自己伙计有问题的,仇家又在后面运作,结果搞半天老张竟然被抓走了,说他给东家吃的饭菜有毒。炭娃刚健,直接来莽的,拿了把厨房的剔骨刀跑去通济场,守到半夜一刀捅死了仇家,然后满身血污跑回家。他老妈看这样子没法了,顾不得关在县牢里的老张,连夜收拾了点东西和炭娃一起跑进山躲回藏区去了。
这事在当时算是个大案,毕竟死了两个人。但那时候正是蜀地军阀混战的时候,慢慢的就没人关注了。老张在县牢里关了一年,无人过问,后来竟然被放了出来。原因是县府为了结案,把两条命的凶嫌都指定给了炭娃,逃去无踪,这案子就结了,这你妈的666……老张出来后还去藏区找过老婆孩子,但他早年买炭娃妈的那个土司已经死了,毫无线索,语言又不通,最后盘缠花完只好一路打工走回彭县,从此孤寡老头一个人过,很惨。
炭娃和老妈进藏区后,最早给人帮工,但太打眼。炭妈是安多藏,说的藏话和当地康区完全不一样(你可以像想广东话对上海话),炭娃自己甚至还不太会说藏话,更惹眼。两年后17岁的炭娃长的更加高大,就由熟人带路,跑到二郎山入了伙,只有这样两娘母才能混口饭吃。
但血饭可不是那么容易吃的,炭娃入伙的这帮人两年之内就被打散了四五次。后来看着实在不行,只得受了招安,最初是当地土司头人拉的队伍,后来辗转到了刘湘手下廖海涛拉的一个暂编团。当时炭娃还没满20岁,虽然人高马大但是脑子比较灵醒,又会一点简单藏语,所以很快在正规部队里冒出了头。先是跟着书记员(相当于后来的文书)识了字,几年后慢慢靠军功混成了排长。廖海涛本人是狮党分子,所以自己部队里上行下效,很多青年军官都被发展成了狮党,炭娃也是其中之一。当时的炮党只能控制长江中下游的几个省,其余省份都是地方军阀说了算。所以川军中的狮党一直是半公开存在的,没得啥子乱党分子的说法。军阀大佬们对各种党,各种会,各种教,其实都是利用的心态,管球得你海外舶来的还是本土自生的,任你吹破大天,只要能保我兵权防区,都是来者不拒。
炭娃加入狮党后,很快被廖海涛推荐去上了当时在武汉的中央军校一个三个月的短训班。在短训班认识了邓锡侯的一个侄儿。炭娃后来发现这娃在学校期间经常和几个其他省份来的老几嘀嘀咕咕。炭娃自己有狮党身份,所以对这种事情很敏感。那几个人其实也来找过他,不过他娃没接招,政治意识还是强。但没想到的是,31年底短训班毕业回四川后,刚回部队报到不久,就被军部从重庆派人来抓了起来。原来有短训班的其他同学回来揭发,炭娃被严重怀疑是复兴社分子,也就是说投蒋了,这在当时的川军中是大忌。炭娃瓜起,被关了好几个月才明白过来多半是给那个邓的侄儿背了锅。那娃是不是被复兴社的人拉过去不好说,但肯定有沾染。邓部和刘部本就不对付,中间恐怕还有点其他瓜葛,总之就是自己给人背锅了。
一直被宪兵司令部关了一年多,廖海涛应该帮他想了办法,但不起作用,一点放人的迹象也没有。后来神军大闹川东北,当地局势糜烂,难民“跑红”如水银泻地一样往四周散,刘湘感觉扶不住了,就在背后拾掇蜀地各路头面人物出来组织安抚会,尽量先把难民稳住。狮党乘此机会出来话事,实控安抚会。狮党大佬从廖海涛处得知炭娃的事后,通过刘湘一个挂名的余秘书出面,折腾一番打通关系,炭娃终于被放了出来。但想再回原部队不太可能,恰好那个邓锡侯的侄儿听说炭娃被放了,差人来请。炭娃犹豫再三,最后还是决定去投邓算了。刘湘这边虽然廖旅长(当时已经升旅长)信任自己,但关系显然没邓那边铁。
直接领导虽然赏识你,但和死保你还差了十万八千里距离。仅仅赏识,显然价值有限。邓那边就不一样了,背锅关一年多,那再怎么也有情分在了,这个可不仅仅是“赏识”就能比的。各位工作了的青年才俊,仔细品吧。
炭娃在邓部一开始被安排做内部军事学校的教官,后来调邓的警卫营当连长。这两职务都很闲,于是他娃就把主要精力放在了狮党上。邓锡侯本人很会做人,其人好客好饮,他的部队比刘湘的21军对狮党分子更宽容。当然炭娃还是聪明,从没在警卫营做过任何狮党活动,对人也保密自己狮党身份。他在邓部发展的同道主要是下面一线部队的人。这娃以这么低的文化程度,能有这个觉悟还是算很牛逼。
大约两年后,35年初秋,炭娃被放到了邓部下面一个旅去任职,驻所在广元附近。炭妈那时已经被接到成都,在北门外找了个小院子暂居。炭娃刚想去和妈打声招呼要走,突然被狮党的联络人某某告知,暂时别去广元,晚上有人来找。
炭娃一直等到半夜,才在门口看到来人,一个穿长衫子,面色白净,三十左右的斯文人。来人说一口带陕西口音的普通话“我姓黄,有一单买卖要做,是两年前救你出来的余秘书把你推荐给我的”
炭娃听来人说完后,只沉默了半分钟就点头“我做!党对我有恩,余秘书对我也有恩,既然专门推荐我,想必不会害我”
黄先生点点头“还有四个人跟你一起,归你指挥,你负实际责任”
“好!”
“部队这边不用担心,你们只管走,我会让人安排好,就当你们请一个月假回去探家,期满回来正常销假就是”
“好……到底要毛哪个?”
黄先生顿了一下,抬眼盯着炭娃“周善培!”
炭娃一愣,这个名字他好像听过,但一下想不起来到底是谁。
周善培是清末蜀地的……你们像想成蒸发委书记吧。这娃是绍兴师爷的后代,老头子到四川当师爷这样举家迁过来的。辛亥的时候这娃掌管蜀地治安,赵尔丰新上任,对政情民情都不熟,过分依赖这个师爷家庭出身的手下,诱捕保路运动各大佬及后来激起成都血案,其实都是这娃在背后捣鬼。革命党醒悟过来后誓杀此人,但辛亥后给他娃跑脱了,窜到上海租界里当寓公。不过你们不要像想成他娃就落魄了,这人的智识是一等一的,民国初年仍然在台面上蹦跶的挺欢,而且酷爱在各股政治势力之间纵横埤阖, 把天下人当猴耍。国人都有明君情节,深恨这种以智凌人的诈谋权术之徒,谓之小人。
当然,这些理由肯定不是有人想杀他的原因。被人盯上只可能是在背后活动时伤到了别人的利益。炭娃也不想搞清楚为什么要去杀这个姓周的,自己只是完成任务而已。何况这娃在蜀地欠那么多命债,被干掉也不冤。
第二天其他四个人在成都和炭娃会合。炭娃一看,都是热血团的人,好嘛,验钢火的时候到了。这里先说说这个热血团:狮党一直油浮于水,过于依赖精英阶层,严重欠缺社会动员能力。这种党在和平时期还能扑腾两下,革命年代只能空了吹,和徒有其表的袍哥也差不了太多。党内更是山头林立,各行其是,大佬们都想把党当成“为我所用”的工具,各个都打小算盘心怀鬼胎。总体来讲狮党其实就是他妈个高端袍哥会。当然,这种形态的团体因为组织力欠奉,对成员的约束几近于无,而大佬又喜欢出风头刷存在感,所以组织内时不时的总会冒出些弹绷子娃娃,喊打喊杀,拯救中华……热血团就是这样一个小团伙,是塘沽协定签订后,狮党和炮党拉豁,川军内激进狮党分子(大多为杂牌军校生)不服整肃命令秘密建立起来的。
炭娃是热血团骨干之一,其他四个人,魏信阳是炭娃在军部发展的下线,孙林是田颂尧部的一个普通参谋,另外两个人没有留下名字。这次这五个人都是热血团骨干分子,全是被黄先生以各种手段找来的。
一个月后五人出发,先陆路到重庆,再坐船往武汉。本来预先的计划,是到武汉后发电报给上海一个叫小陈的人,等他回电就立即坐船到南京,然后电话再联系小陈,安排好后坐当天晚上的京沪快车到上海,白天行动,搞定后连夜上船原路返回。这样安排的目的是尽量在上海少呆,几乎不过夜。以当时的生活环境和交通条件,这安排其实很不错。但没想到,五人到武汉发了电报住下后,竟然迟迟等不到电报回复,拖了将近一周。这五人除了炭娃在当兵之前吃过血饭,社会经验丰富外,其余四个其实都是十来岁就当兵的人,碰上这种情况全他妈懵了。这伙愣头青之前倒是杀过人,但几乎都是在内战战场上,玩这种社会化活路完全外行。五个人带了八把驳壳枪,子弹N多,每个人腰杆上都鼓一大坨,这他妈是打算去抢运钞车哇?
迟迟等不到电报,炭娃只好决定先在武汉住下来,然后又给成都黄先生电报联系,回电只有一个字:等。
这一等就等出了事。五个人带了太多枪和子弹,又住在一起,不打眼是不可能的,很快被汉口社团盯上。这些码头地界的社团,都是老江湖老油子,看人很准,基本上估出来了这五个人是当兵的在干私活,于是就动起脑筋。五人里面那两个没留下姓名的,闲来无事,这次经费又足,于是日嫖夜赌打发时间,没几天就被当地社团下套,扣了其中一人,让另一人回来拿钱去赎。炭娃一听,火冒三丈,但很快冷静下来明白是被人讹上了。江湖上这种事太平常。现在五人有大事在身,万万不能出岔子。炭娃先开始准备答应对方赎人,但对方要价太高,哪怕把随身带的烟土(准备到南京上海时顺便倒卖赚点钱的)都折了也不够数。炭娃最后决定:来硬的。反正老子手里有枪,怕个屁!
结果没啥说的,被扣住的那个当场被社团打死,报信的那个从船上跳到江里淹死了,信阳左手中了一枪,幸好只是皮肉伤,炭娃把脚跑崴了,只有孙林留旅馆看东西得以幸免。八把枪只剩下四把,烟土也被对方全部抢走……可谓一个惨!在别人码头上来横的,怎么可能全身而退。别人就是吃准你在干见不得人的事,不敢报官。你带着枪也不起作用,反而还会动心思怎么把你枪也给抢了,你敢闹大吗?说白了热血团这伙人还是太年轻,完全是给别人送人头。你们可能会问,明知这伙军阀部队里的青年军官根本没有干暗杀的经验,那个黄先生为什么还要来找这帮年轻人去干买卖?
你说呢?
逃回来后,炭娃发现他们钱也没剩多少了。给信阳看了租界的外国医生(外面的怕被点水),又花一笔钱。这下只够几天的饭钱了,别说还欠着房费的。走投无路之下,炭娃只好又给黄先生打电报,汉口遇贼,钱土皆失,急需救援。
过了五六天,剩下这三个人快饿死的时候,一个面色白净,长相端正斯文的年轻人风尘仆仆的赶到了他们藏身的小旅馆。进门后环视一圈,看着三个人笑笑“鄙人姚明益,受黄先生嘱托,来接应你们……哪个是张呈华?”
炭娃起身,伸手出来“我是”
明益和他握手“从现在起,一切听我的!”
三人面面相觑,信阳口气有点生硬“凭啥子听你的?”
明益点点头“这是黄先生的意思……光凭你们,到不了上海,别说完成任务了”
炭娃想了想,问“兄弟哪部分的?”
明益笑笑“我跟你们是同志(意思都是狮党),但不是当兵的,我是读书人”
这个叫姚明益的年轻人到了后马上要解决的第一个问题,就是要不要去给那两个死了的收尸?你们看电影电视剧的话,是不会碰到这种问题的,因为这问题太现实,出现在情节中太让观众尴尬。大家都是来看主角表演大杀四方的,鸡毛角色死了就死了呗,还收尸,是不是还要演拉屎?但在当时的环境中,收尸确实是一个非常现实的问题。大家都是狮党人,是同志,更何况谁不是爹妈生的,就这样让人客死异乡连骨灰都没有?但真要去收尸的话,就可能会爆线。三十年代的中国,虽然四处不太平,但在武汉这种大城市,尤其还是租界里面,法律任然还是有点作用的,景察不是摆设,和电视上演的不是一回事。明益考虑再三,最后对三人说,自己一个人去想想办法,你们好好呆着养伤吧。
那时候的租界市政管理其实并不差,无名尸有类似于教堂下属公益社一类的组织在管。明益通过旅馆老板找到了那个公益社,给了钱,把两具尸体都火花了,骨灰暂存。这种公益社只是名义上由外国人教堂管的,实际上干活的人和小头目都是本地社团分子。明益很清楚这点,果然第二天就有两个人找上门,本地社团探底来了。明益面不改色“他们在贵码头走水翻船,和我没关系,我是重庆唐大爷的人,受命来处理后事,请各位行个方便,不要为难我”
对方有点惊讶,想了想“这两个是唐廉江的人?”
明益摇头“不是。唐大爷受人所托,只负责后事而已”
对方掂量了下,没说什么,走了。
几天后去南京的船上,炭娃和明益站在船舷处看夜景。炭娃说,你娃胆子大哦,不怕对方看出破绽?明益叹口气,看出了也无所谓,他们只是想确保打死我们两个人不会有后续麻烦。炭娃心里吃惊,转头看了看明益,这个穿着合身旧西装的年轻人面色凝重,一言不发的盯着江面在发呆。
当时明益自己也才23岁,比炭娃还小4岁,此去上海滩,前路未卜。
到南京后,四人找旅馆住下,然后给上海打电话,打了多次才终于联系上那个小陈。然后过了两天,在南京见了小陈。这娃很瘦,面相有点凶。明益只带了炭娃去见面,没想到对方开口就说,要两支枪加两百发子弹。明益一愣,看炭娃,炭娃也在看他。黄先生当时交代的,这个上海小陈是个早已安排好的内线接应,但你妈看这架势,难道是道上混的?明益拿捏了下语气和用词“我们总共只有四个人,我还是读书人不会使枪,总共就三把枪一百多发子弹,这要是给你了……我们任务可没法做了”
对方撇撇嘴“一把枪十颗子弹就能干,有什么不能做的?没我,你们才是真的不能做。上海那么大,你们连周善培在哪都找不到。而且他是每月在捕房交保护费的人,就算知道了住哪,他住所附近24小时都有景察,你们也没法下手”
明益埋头斟酌了半天,转头看看炭娃,炭娃轻轻点头,于是明益对小陈说“枪只能给一把,子弹30颗,其他的我们真不能给了,不然就算全身而退回了四川也没法在部队里交代”
过了几天,四人突然在报纸上看到一条消息“汪先生被刺”,吓了一大跳。明益越想越不对劲,炭娃说,要不我们先去上海躲躲?明益想了想说,不行,现在汪被刺,我们离开南京的话很容易招人怀疑,只能干等小陈了。
大半月后小陈来电,安排好了。
当天晚上四人上了京沪快车,到上海时半夜12点,小陈叫了个司机开车来接。这辆车是租车行的,司机把他们扔到英租界的一个咖啡馆附近,交给明益一封信,然后开车走了。信是小陈写的,大致画了个周善培的面貌长相,然后说这娃早晨九点会在这咖啡馆露面。四个愣头青商量了下,呈华决定趁现在夜色还未深,街上仍然有人,赶紧踩点,熟悉环境,然后撤退路线走两遍。这一通折腾完了,四个人已经困得不行,决定就在咖啡馆附近一个街角杂货铺门口咪几小时算了。
几小时后天亮,一切正常。四个人找了个早点摊随便吃了点,就在咖啡馆斜对面报栏那里歪着,等周善培露面。九点左右,周善培真来了,但没想到的是,他不是一个人,另外还有两人和他一起的。明益按计划,独自一人施施然也进了咖啡馆坐起,点了杯咖啡,观察。
观察了半小时,目标三人一点散场的意思也没有。明益知道不能再等了,万一他妈这三人一直聊到吃午饭呢?就算结束了但走的时候三人也一起走呢?周善培不一定会落单,一直傻等很可能会出问题。于是明益结账出门,转过街角,悄悄告诉炭娃,不能再等了马上下手!
炭娃和信阳一言不发,疾步前后脚走进了咖啡馆,进去就一人一梭子(驳壳枪连发)。但毕竟愣头青,明益刚才出来后忘了告诉炭娃一个很重要的情况:周善培他们坐的是一个靠窗的角落,那天不知什么原因那个角落的大窗帘没拉开,他们桌子那一块光线很差。炭娃和信阳其实根本就没看清哪个是周善培,本身光线太暗也看不清楚,于是干脆一通乱打。根本就不是杀手干的事,这不是暗杀,这他妈是屠杀。但周善培这边三个人那天真的是运气爆棚,周本人一听到枪声根本没反应过来,身体条件反射一下缩到了桌子下面;另一个T先生一把将他们的桌子掀了挡在前面(T先生这算是逃过一劫,不过抗战爆发后没多久在法租界仍然被军统暗杀了);另外个L先生离炭娃他们最近,虽然第一时间后背就中枪,但这娃是社团人士,自己身上也带着枪,倒地后摸出枪就一口气把子弹对着后面全部打完。炭娃和信阳见对方有枪,不敢继续多呆,胡乱把弹夹打完后立即跑了出来。
是不是感觉这暗杀太菜了,简直形同儿戏?热血团这伙人本来就是愣头青,除了当兵早,打过仗,玩枪熟练,其他的跟普通人比根本就没什么优势。那为啥被挑中?说了的嘛,愣头青。
炭娃和信阳按原定计划跑到街角,刚和孙林会合,咖啡馆那边巡捕的哨子就开始响了。三个人闷头钻进小巷。炭娃和信阳在前面飞奔,甚至都顾不上把空弹夹换掉。孙林在后边断后,离炭娃他们几十米远。巷子有个岔道口,炭娃和信阳刚跑过去,就有两个黑警服巡捕从里面冲了出来,孙林在后面抬手就开枪,巡捕还击。乒乒乓乓一阵后,无人中枪,但炭娃和信阳在前面跑没影了,孙林没办法,只好返身又跑回大街上,东躲西藏埋到了人群里去。
明益在踩点出来后立即就喊了个黄包车离开了。这是先说好的,他是书生读书人,留在现场只会添麻烦,关键他有更重要的事:按约定地址去找小陈安排撤退上船。但明益在约好的地方没见到小陈,只被人带到一个阁楼上躲了起来。到了中午,炭娃和信阳也来了。没想到信阳竟然中弹了,肚皮上挨了一枪,应该是在咖啡馆被对方打中的。手枪子弹威力小,伤口不大,但信阳人已经快站不起来。而且孙林一直都没来,也不知是死是活。
在那个阁楼上躲到傍晚,信阳已经快不行了。伤口没流多少血,但关键是子弹一直在体内,不动手术或者不暂时消炎处理的话,以那时候的卫生环境和医疗条件,分分钟格屁。热血团都是打过仗的人,这些是常识。但外面风声鹤唳,一上午就封了三次街(巡捕在街道的两头扯绳子拦死,然后逐个清查路人),现在把信阳背出去看医生的话,几乎百分之百会爆线。唯一的办法就是等到半夜喊黄包车悄悄拉出租界进华界,在那边找小诊所偷偷处理。但现在孙林一点音信也没有,等还是不等?
快半夜12点的时候,来了个30岁左右穿呢大衣的人,进屋后打量一圈,然后自我介绍说姓顾,是黄先生的朋友,这边余下的事情由他来收尾。不过这位老顾坐下后却说,上个月汪先生在南京被枪击,现在准备出洋,目前还留在法租界,现在不论是法租界还是英租界,当局都相当紧张,怕又出事,现在租界警务处都收假了,所有人全部在岗24小时待命。你们干的这买卖手脚不利索,周善培和一起的T先生毫发无伤,只有另外那个开枪还击的L先生挨了两颗子弹,不过也没事死不了。但这位L先生不是普通人,他哥哥是工部局在任华董,现在事情已经闹大,刚才晚报已经登出来了,你们还没看吧?老顾说完从大衣口袋里扯出一张折叠的报纸递给几个娃。
明益看完后想了想,盯着老顾“这意思是我们走不掉了?”
老顾脸色凝重,顿了好一下才回答“要走也不是没办法,但……”
“什么?”
“得交人出来!”
明益和炭娃信阳对视一眼,然后转头问老顾“黄先生知道吗?”
“我还没来得及给他打电报,不过这种套路,他应该猜得出来”
明益点点头,没说话了。
沉默了几分钟后,明益很平静的对老顾说“我去”。炭娃想制止明益,已经来不及。明益从包里掏出一个信封交给炭娃“里面有我成都亲戚家的地址,你们如果能平安走脱,路过武汉的时候记得把那两罐骨灰取出来带回四川去,然后回成都后去我亲戚家给他们说一声,就说我在上海出长差......”
炭娃还想说点什么,但无法开口。他和信阳都是军人身份,如果爆线被抓,影响太大。而且现在信阳已经快撑不住,除此下策外也没其他办法了。由明益这个书生去自首其实是最合理的方案。但谁又真愿意把自己送牢里去扛事呢?这次这事没死人,交人出去其实问题不大,黄先生肯定会想尽办法争取最好的结果。不过再怎么说也是扛事,而且是在人生地不熟的上海……信阳挣扎着坐起来和明益握了手,炭娃用劲抱了下明益。三人就此话别。
炭娃再见明益已是六年以后。信阳三年后牺牲在山东抗日战场,和明益再未相见。
明益和老顾出门的时候,还转头告诉炭娃,不要再等孙林了,你们能走脱一个是一个。小孙脑子活络,现在说不定已经跑出上海。